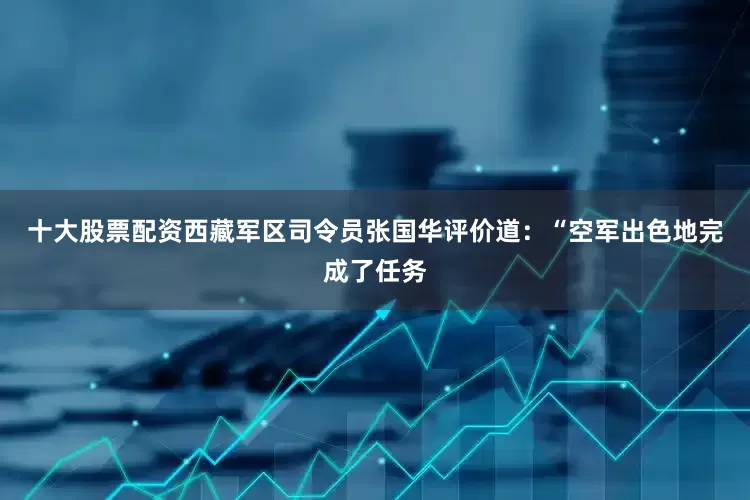
上一期文章推送后,不少读者通过私信和评论区留言,对图-4轰炸机的获取方式——究竟是“购买所得”还是“苏联赠送”——表现出浓厚兴趣。因此,在今天视频的开篇,我们先针对这一疑问展开一次简短的考证说明。
图-4在中国曾长期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公开可查的资料十分有限,但偶尔仍能找到一些关于它“是买是送”的零星记载。
首先,曾隶属于空36师(即图-4所在部队)的退休干部,多数都明确表示这款飞机是通过购买获得的。
例如,原空11军军长、曾任空36师副师长的张国祥就提到,这些飞机是“国家耗费巨额资金购入的珍贵装备”。他还进一步解释道:“以我个人的判断,最初斯大林或许承诺过将其赠送给我们,但后来他去世了,赫鲁晓夫又向我们收取了费用。”
原独立第4团飞行员王圣文也有类似表述:“关于图-4进入中国的缘由,存在多种说法,实际上这些飞机是我们支付款项购买的,而且苏联方面的报价高达2亿美元。”
与之相反的是,空军林虎将军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一书中写道:“图-4是苏联在1946年仿制美国B-29飞机制造的机型,1953年3月,苏联向中国赠送了10架该型轰炸机。”

除了获取方式众说纷纭,公开资料中关于图-4的装备数量,记载也各不相同。我查阅到的数字主要有三种:10架、12架和13架。其中,原空11军军长张国祥的回忆可信度最高,他表示自己在80年代曾亲自为“13架图-4”办理过退役手续。由于张国祥在图-4所在部队工作了近30年,这个数字他大概率不会记错。
以上就是对上期文章读者疑问的简要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回归今天的核心主题:图-4重型轰炸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客观而言,中国引进的图-4数量虽不算多,却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服役期间,图-4完成了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任务,为中国空军乃至整个国家的国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图-4的机身尺寸足够大,起飞重量超过60吨,机组成员达12人,燃油和弹药的装载量远超轻型轰炸机。它的常规续航时间长达18小时,即便在恶劣天气或高油耗的情况下,也能保持10小时的持续飞行能力。
该机型配备了航行雷达、天文罗盘以及远程无线电高度表,其轰炸瞄准具不仅能自动追踪目标,还可与操纵杆联动,由轰炸员直接操控飞机实施轰炸。为此,图-4专门配备了航行、轰炸、雷达三名领航员,确保飞机在作战、巡航等各类场景下都能灵活应对。
这样的性能在当时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即便现在,我们也能想象到,在50年代初,当这款性能优异的重型轰炸机列装时,空军部队官兵们内心的激动与振奋。
1953年3月15日,中国首支重型轰炸机部队——独立第4团在石家庄正式组建。当时中央军委的规划是,以这个团为基础,逐步构建起我国自主的战略轰炸机部队体系。

能够入选独立第4团的成员,都是从各部队挑选出的政治可靠、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且技术过硬的飞行骨干,每个人都以加入该团为荣。但在团队组建初期,他们面临的条件却极为艰苦。
起初,他们驻扎在石家庄郊区某部队的农场里,8名飞行员挤在一间仅有4张上下铺的宿舍中;用餐地点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子,一旦刮风,菜汤表面就会落上一层尘土。
事实上,中国一直高度重视重型轰炸机的发展。早在图-4交付前的1952年,空军就从航校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学员,派往苏联学习图-4的驾驶技术。苏联方面安排中国飞行员在莫斯科附近的梁赞地区接受培训,并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生活保障。
据曾赴苏学习的飞行员王圣文回忆,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日常饮食中经常能吃到肉类和牛奶,偶尔还会供应烤鸡。不过,让王圣文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在苏联洗澡的经历。
他提到,去浴室时,脱下的脏衣服直接放在更衣室即可,无需自行处理;洗完澡后,能领到熨烫得平整如新、还带着肥皂清香的干净衣物。这段经历让他多年后仍记忆犹新,感慨“在苏联洗澡真是一种享受”。
1952年底,完成学业回国的飞行员们在石家庄集结,在这里继续接受苏联教官的新一轮培训。为确保保密,所有学员外出时必须换上便装;每天课程结束后,教材和课堂笔记都要交给保密员统一保管;若有人不慎将记录学习内容的废纸遗落在教室,还会受到相应处分。
从这些细节不难看出,空军对图-4轰炸机的列装极为重视。
1953年,苏联移交的10架图-4被编入独立第4团。全团共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三个机组,再加上团长直接指挥的一个机组,恰好组成十个机组,与飞机数量相匹配。

独立第4团在石家庄驻扎的时间并不长,随后便转场至北京南苑机场。原因是图-4机身过重,石家庄机场原本供歼击机使用的跑道已被压损。然而,转场至北京南苑后,跑道承重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直到陕西武功的新机场建成,图-4才终于有了首个正式的驻扎基地。
1954年,10架图-4参与了国庆阅兵仪式,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它们一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956年3月28日上午,独立第四团接到空军司令部命令,要求立即出动图-4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支援康巴地区政府机关坚守待援。自此,图-4正式投入平叛任务的执行。
起初执行任务时,由于高原地区没有可用的机场,飞机必须从陕西武功长途飞行至战区。后来,兰州军区在青海格尔木一处盐层厚度达七八米的盐湖上展开机场建设:通过抽取卤水填平盐层表面的坑洼,再进行碾压平整,一座全新的机场就此建成。
有了这座盐湖机场,重达60多吨的图-4不仅能在高原顺利起降,而且该机场的净空条件十分优越,轰炸机部队得以在此开展高原作战训练,积累相关实战经验。
但盐湖机场也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弹药运输成本高昂,同时面临缺水、缺蔬菜、缺氧等困境。此外,当地空气中盐分含量极高,即便在夜间睡觉时,也会让人感到不适。因此,尽管起降条件尚可,但平叛任务一结束,这座盐湖机场就停止了使用。

在青藏高原执行任务的图-4轰炸机,堪称不折不扣的“多面手”:除了执行轰炸任务,它还需承担侦察监视、散发传单、投放补给等工作,几乎各类任务都有涉及。
例如,它们经常为地面部队空投急需的大米、食盐,以及当地流通的硬通货银元,有时还会为伤病员投放氧气袋。
对于一些长期执行任务、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地面部队,他们还会请求空投报纸。独立第4团会专门搜集近期的报纸杂志,搭配一些空勤灶的巧克力和水果罐头,连同慰问信一同空投给地面部队。这一举措极大地鼓舞了平叛部队的士气,也增进了空军与陆军之间的战斗情谊。
有一次,陆军某连在追击残匪时与大部队失联,在野外断粮长达一周。图-4紧急出动,经过近两小时的搜索,终于找到了该连队。随后,图-4与伊尔-12运输机协同作战,向目标区域空投了大量物资。事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评价道:“空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挽救了100多人的生命。”
相较于空投任务,图-4执行的轰炸任务要惊险得多。
当时,我军面对的叛乱分子中,有部分战斗力较强的骨干成员:他们单兵作战能力不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是远超我军。
在野外环境中,他们只需裹上皮衣就能入睡,几乎不受高海拔气候的影响;日常携带美制加兰德步枪,枪法精准,还擅长使用腰刀进行格斗。但这些叛乱分子作战时缺乏组织性,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没有协同配合,各自为战,占据优势时一拥而上,战局不利则四散逃窜。

尽管我军官兵的军事素养远胜叛乱分子,但在高原作战中,由于无法携带重武器,当遇到匪徒依托坚固的石头堡垒负隅顽抗时,就需要空中支援。
有一次,大队长张国祥执行对敌支援任务时,地面部队指示了一个直径仅2.3米的石头碉堡。当时飞机飞行速度达每小时数百公里,飞行高度为数百米,机组人员密切配合,轰炸员精准瞄准,一次投下四枚炸弹,其中一枚直接命中碉堡。对于没有制导功能的常规炸弹而言,这样的命中精度堪称出色。
不过,另一次未能完成的轰炸任务,却让独立第4团的许多飞行员难以释怀。
1959年3月,驻扎在青海格尔木的0044号和0042号轰炸机接到命令:有一股叛军正往雅鲁藏布江方向撤退,存在外逃迹象,需立即起飞两架轰炸机前往该区域侦察。
两架图-4很快飞抵雅鲁藏布江沿线,但江两岸树林茂密,为叛匪提供了极佳的掩护,机组盘旋许久也未发现目标。经过长时间搜索后,0044号轰炸机的轰炸员终于报告:“江面上发现几艘橡皮舟。”
飞行员略微降低飞行高度,轰炸员再次观察后报告:“并非橡皮舟,而是牛皮船,共三艘,其中一艘较大,两艘较小。”为了进一步确认情况,0044号再次降低高度,这次轰炸员的报告更为清晰:“船上人员中有穿红衣服的,也有穿黄衣服的。”
机组立即将这一情报上报,指挥部回复:“密切监视其动向,牛皮船内很可能搭载有叛军高层人物。”
0044号轰炸机在飞行员王圣文的操控下,持续围绕三艘小船盘旋。不久后,通讯员又监听到一个重要情况:“受到地面电波干扰,牛皮船内携带了电台!”
三艘牛皮船、红衣与黄衣人员、外加电台——这些关键信息被再次上报,两架飞机在空中焦急等待指挥部的下一步指令。

终于,指挥部的命令传来:“这很可能是大和尚(达赖喇嘛)准备叛逃,立即做好轰炸准备。”
王圣文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沉稳地操控飞机转向,将机头对准三艘牛皮船,进入轰炸航线。随后,他将飞机控制权移交轰炸员,机上的瞄准仪成功锁定了最大的那艘牛皮船。
“开启弹仓。”轰炸员按照轰炸流程进行通报,再过几秒,炸弹就将投下。就在此时,无线电中突然传来指挥部的声音:“0044号,解除轰炸!立即解除轰炸!”
王圣文以为自己听错了,连忙回复:“请重复命令,请再次重复命令!”
无线电中再次传来指挥部的指令:“解除轰炸任务,立即返航!重复,解除轰炸,立即返航!”
“0044号收到,立即返航。”
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这个瞬间,王圣文依然难掩心中的遗憾。他说:“虽然我们心里有太多不解,但命令就是命令,容不得半点违抗。于是我们关闭弹仓门,调头向格尔木返航。”
直到叛乱彻底平息后,这次突然取消攻击命令的谜团才被揭开。
当时,独立第4团参谋长赵吉星前往西藏军区开会,见到了司令员张国华。他向张国华问道:“当初为什么不让轰炸那艘牛皮船?”张国华回答:“那时没法向飞行员详细解释,只能先取消任务。根据你们的报告,再结合我们掌握的情报,可以确定那三艘牛皮船上的人就是老和尚(达赖喇嘛)及其随从,那个穿黄衣服的,就是他本人。”
“我们当时立即将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回复说不炸。还提到,他将来要是反悔了,或许还会回来。”
赵吉星又追问:“不炸的话,他不就逃到国外去了吗?”张国华反问道:“那又如何?等到将来全世界都实现共产主义了,他还能逃到哪里去?”

以上这段往事,源自飞行员王圣文的回忆。王圣文在独四团服役至1968年,之后被选调到成都的航空部门担任军代表。
作为人民空军首批图-4飞行员,即便离开了轰炸机部队,他依然始终关注并投身祖国的航空事业。2006年,王圣文老人与世长辞。他生前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离开了战略轰炸机部队,告别了朝夕相伴的飞机与战友,但我从未忘记我的图-4,我最亲密的伙伴。”
相较于图-4在雪域高原的战斗经历,将其改装为“空警一号”预警机的故事,更为人熟知,也更让人感到遗憾。
长期以来,我国地面雷达系统存在诸多监控盲区,尤其是在漫长的海岸线附近,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为改善这一状况,预警机的研发被提上议事日程。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军队与地方共十几个部门联合启动了预警机研制项目。
当时的计划是,将一款苏联地面雷达进行简易改造后加装到飞机上,而在当时的国内,唯一能承载雷达天线及相关设备的载机,只有图-4。因此,这项改装任务再次交给了独立第四团所属的空36师。
要加装雷达,首先必须更换飞机上现有的老旧发动机——这些发动机大多已接近使用寿命上限。

当时我国库存中有一批新发动机,是此前购买苏联伊尔-18运输机时配备的备用涡桨发动机。在武功附近的飞机大修厂内,工作人员为一架图-4换装了四台新发动机。随后,这架图-4又进行了机身加固,并安装了每分钟可转动2.8圈的雷达天线罩。
1971年6月13日上午,106团团长孙勇率领机组驾驶“空警一号”完成了首飞。改装后的“空警一号”机身重量为38吨,最大起飞重量53吨,实用升限10200米,最大航程4000公里,留空时间7.5小时。经过多次试验与后续改装,飞机的飞行性能最终达到标准,但接下来的雷达测试却陷入困境。
测试过程中发现,这部雷达在飞机上向空中探测时效果尚可,能在2000米高度发现200公里外的安-24飞机;但向地面探测时,却无法过滤地面杂波,雷达荧光屏上满是干扰信号,根本无法识别目标。
在青海湖和渤海海域进行海上测试时,这部雷达也只能在海面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发现320公里外的船只;对于飞行高度低于预警机的空中目标,则完全无法探测。
曾参与“空警一号”研制的张国祥认为,即便当时雷达性能达标,“空警一号”的发展前景也并不乐观。
他解释道:“就算雷达没有问题,当时的‘空警一号’也无法引导我方战机拦截多批次敌机,不能实现全方位作战指挥,达不到最初的设计要求。要实现这些功能,需要高性能计算机的支持,而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

张国祥还提到,在研发“空警一号”时,图-4的机身寿命已不容乐观——毕竟这款飞机从1953年就开始服役,已属于老旧机型。同时,当时国内也没有其他机型能替代图-4作为载机平台。因此,“空警一号”如同昙花一现,其坎坷命运从项目启动之初就已注定。它最终的遗憾结局,不能仅仅归咎于雷达技术的失败。
关于图-4,我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在此可简要总结:自1953年服役以来,图-4先后完成了开辟高原航线、首航当雄机场、参与平叛作战、打击东南沿海P-2V侦察机、为珠峰登顶提供航测保障、改装电子干扰机、研发预警机、投放无人机等多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
直至80年代退出现役,图-4从未出现过战斗损失或重大飞行事故。这一方面得益于苏联制造的耐用性,更重要的是部队日常的精心维护与保养。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说:我们不仅应当铭记图-4这款功勋机型,更应当铭记那些驾驶它、保障它完成任务,并为此默默奉献的所有人员。
广盛网配资-散户怎么加杠杆-网上股票开户-十大股票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